
道德诠释者,怪
文章大思考者+解释者
通过世界杯2022淘汰赛对阵2021年9月14日
在一个无处不在的媒体报道任何事情的时代,大多数人每天都能看到指责行为。但责备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怎么做呢?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2019-20年森林大火期间,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因在环境危机期间度假而受到指责。在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高峰时期,澳大利亚的抗议者指责个别警察和逍遥法外的人对原住民进行了历史和现在的暴力虐待。
也许你还在责怪你那过于愤怒的高中老师让你变得焦虑。也许你最近责怪你的同事放了你每周的Zoom电话的鸽子。
不管风险有多大,我们都熟悉指责,但你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吗?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指责被认为是我们对那些我们认为违反了道德规范的人的负面反应,让我们感到委屈。
有几种指责的理论它们探索了对它究竟如何工作的不同解释,但最主要的区别是它如何或是否被传达。
一方面,我们有交际责备——这是一种外在行为,表明一个人因某事责备另一个人。当我们对闯红灯的人大喊大叫,在社交媒体上责骂政客,或者告诉某人我们对他们的行为感到失望时,我们是在交流指责。有时,责备甚至可以通过我们说话或行动的微小方式巧妙地传达出来。
有些人认为有必要进行责备的交流——没有这种公开的责备并不是责备。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可以有内在的责备,一个人从来没有公开承认他们因为某事责备别人,但仍然有一个内化的判断、情感或欲望——想象一下,一个人对一个搬到世界另一端却不再和他们说话的朋友怀恨在心。
当我们想到指责时,我们必须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要指责,它有什么作用,什么时候是可以的?
一个常见的答案是历史,尤其是宗教。例如,在《圣经》中,责备常常被认为是让我们承担责任和阻止异议。指责经常(现在仍然)被用作衡量公民和/或政府能接受什么行为的社会和政治指标。
当我们考虑交际性责备时,这一点更加明显。举个例子,澳大利亚公众和新闻媒体在总理森林大火假期期间对他的指责。这些表达从简单的表示不满,到更复杂的表示渴望改变和对道德缺陷的严肃承认。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在2021年新冠肺炎每日新闻发布会上,各种政治人物迅速传达了他们对各种无视公共卫生命令的人群的指责。
但是这种类型的行为总是可以的吗?它总是有效的吗?这些都是伦理学家在思考诸如指责之类的问题时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思考这些问题的一种方法是通过不同的伦理框架来看待它们。
结果论告诉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行为、性格、态度等的结果。结果主义者可能会认为,如果责备会导致更糟的结果,我们就不应该互相责备后果总比我们保守秘密要好。
例如,如果一个孩子做错了什么,结果主义者可能会说有时候这样做更好不表面上责备他们,而不是做其他的事情。也许给他们改正错误的工具,或者表扬他们在情况的另一个方面做得很好。
然而,不那么直观的暗示是,有时会是这样错误的因为某事责怪某人,即使他们罪有应得!假设你有一个朋友,他非常特立独行,故意做错误的事情来引起别人的注意。有些结果论者可能会这么说错误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在鼓励这种行为,因为他们想要被指责的注意力。对于那些认为别人被指责是罪有应得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
一个论可能会在这里帮助他们,告诉他们如果有人应该受到谴责,那么他们应得的该受责备的是我们责任去责怪他们,不顾后果。一些义务论者可能会说,只要我们的意图是好的,那么我们就有责任指责做错事的人,让他们看到他们的道德缺陷。
随之而来的是一些不同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有义务去责怪那些“罪有应得”的人?在责备会产生非常糟糕的后果的情况下呢?我们仍然有责任为他们的错误指责他们吗?
下次当你责怪别人的时候,想想你的意图和你想通过这样的行为达到什么目的。也许你最好还是把它藏在心里,或者找一种更积极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也许责备是最好的结果,或者也许你确实应该把沮丧发泄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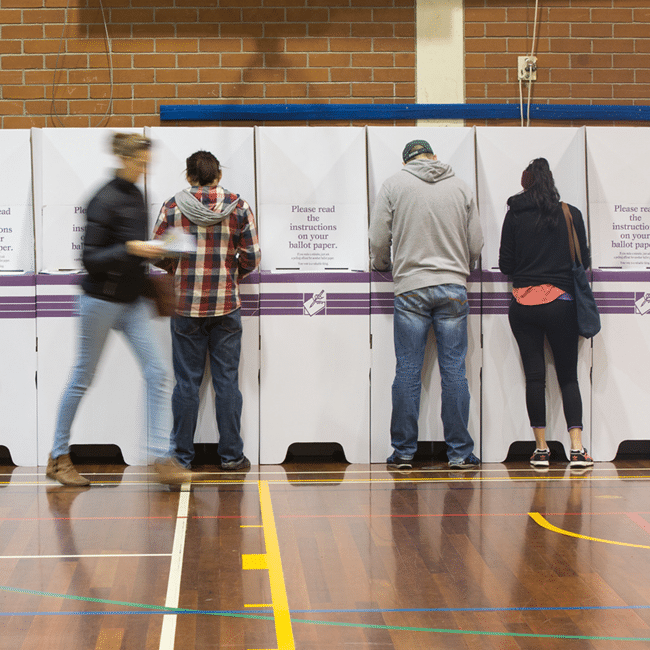
加入谈话
责备在你的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